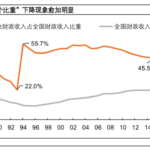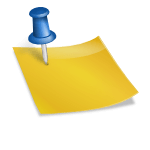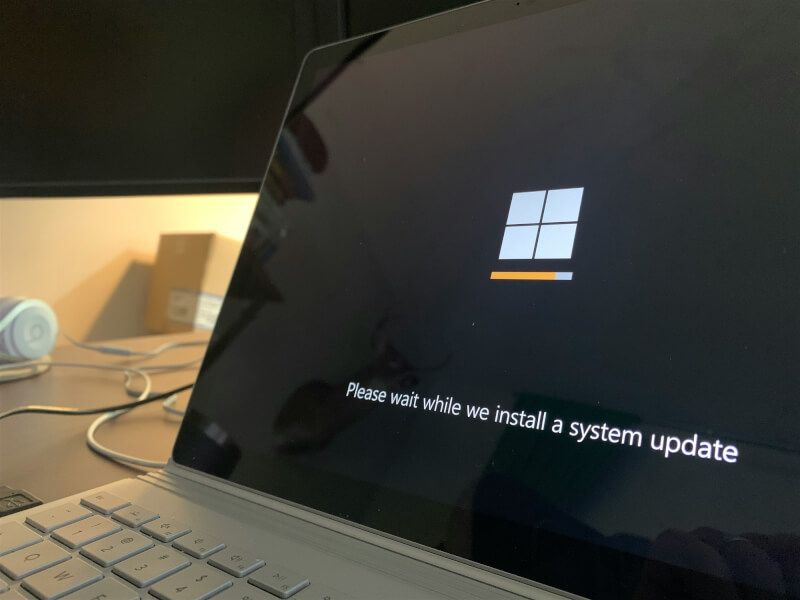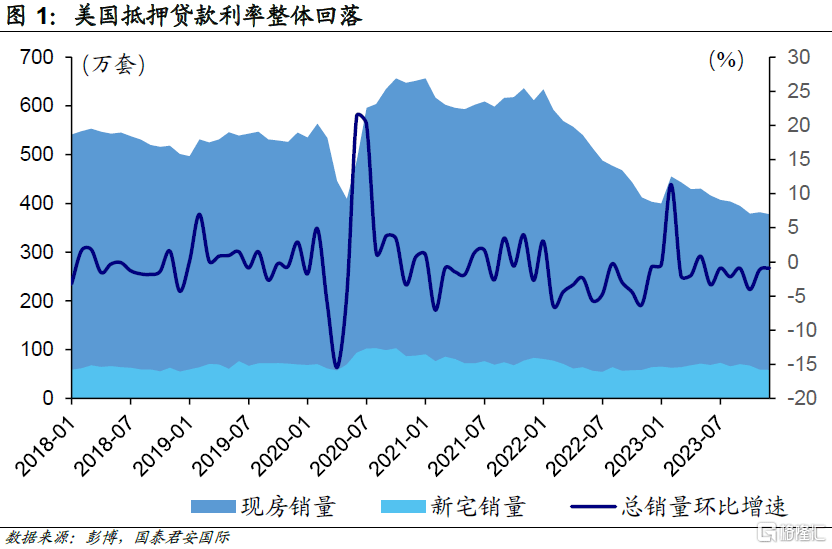[ad_1]

(中央社東京17日綜合外電報導)日本名古屋大學研究所的研究團隊本月發表一項實驗結果指出,在紙上寫下自己憤怒情緒後,把紙揉成團丟進垃圾桶或送進碎紙機,有助平息怒火。
日本時事通信社報導,研究小組成員、名古屋大學教授川合伸幸說:「這是個簡單且有效的方法,希望大家可以在職場和家庭中運用。」
英國自然出版集團(NPG)旗下的綜合自然科學期刊「科學報告」(Scientific Reports),本月刊登了這項實驗結果。
在這項實驗中,研究團隊首先刻意對受試者所寫文章給予低評價,像是「你寫的文章不符合大學生的程度,希望你多多讀書」等,引發受試者產生怒氣。
接著研究人員要求他們盡量客觀地把憤怒原因寫在紙上,例如「我的文章被侮辱了」,並將受試者分為3組後,觀察他們的情緒變化。
這3組分別是把紙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、把紙放進碎紙機,及僅將紙收進箱子裡。
而研究人員將憤怒程度分為6種後,依照程度訂定不同的數值以便進行量化,並在3個時間點測量「憤怒指數」,分別為實驗開始時、感受到文章被批評之際及實驗結束時。
實驗結果發現,把紙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的組別在實驗結束後的「憤怒指數」降低了1.47分,幾乎降至與實驗開始之際相同;而「碎紙機組」也降低了1.16分。
另一方面,只是把紙收起來的組別,「憤怒指數」僅下降0.81至0.49分。
川合表示,沒想到部分受試者的憤怒指數可以降到與實驗開始時差不多,而用電腦打下生氣原因並將文件移到「資源回收筒」後按下「清理資源回收筒」的方式是否同樣有效,還待驗證。(譯者:楊惟敬/核稿:黃名璽)1130417
標題:生氣時如何有效平息怒火?研究:紙上寫憤怒原因丟垃圾桶
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爲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有侵權行爲,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
[ad_2]
![睽違近一年再度嘗試 日本發射主力火箭H3二號機[影] 2000x1397_wmkn_42243186060807_0.jpg](https://techroomage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2/2000x1397_wmkn_42243186060807_0-150x150.jpg)